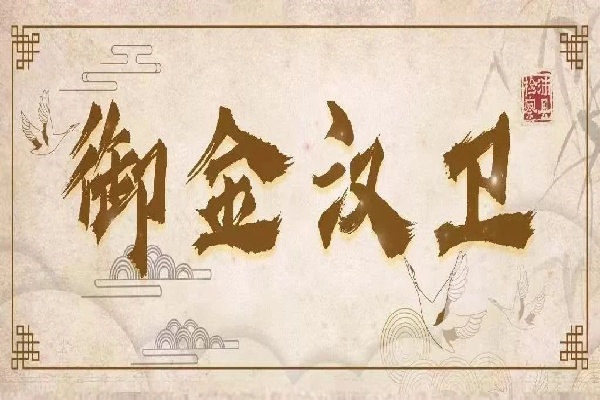在绵延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吏治是否清明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因而,历朝历代统治者对于吏治都十分重视,从加强倡廉笃勤制度建设入手,力求纲纪齐备,吏治端正,社稷存续。
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等级社会,位高权重、至尊至极的
纵观封建社会演进历程,尽管政权递嬗、朝代更迭,但倡廉笃勤制度建设却是为封建统治者历来所重视的。
历史是在辩证中发展前进的,有腐败现象,必然就有反腐败的思想与制度。先秦时期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在提出治国安邦理念的同时,开始着手研究制定倡廉笃勤的法律制度。从史籍上看,他们从统治经验的积累中,认识到封建官吏既须清廉节欲,又要励精图治;廉政是止贪防乱之本,勤政是廉政的基础,因而对“吏治”采取廉政与勤政一起抓。
楚国吴起认为:“大臣太重,
《为吏之道》指出:“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荷,审当赏罚。”这和后来各封建王朝编写的被称为“可为牧令圭臬”的“官箴”一样,实际上都概括地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对官吏的廉政与勤政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
当时,司法官吏凡是不能及时发现辖地犯罪活动的叫“不胜任”,“知而弗敢论”的叫“不廉”,处刑失重失轻的叫“失刑”,判罪或重或轻的叫“不直”,故意让犯人减刑或逃脱制裁的叫“纵囚”,都是违法失职行为,要受到严厉处罚。
中国封建法律自秦律开始,在“吏治”方面始终围绕倡廉笃勤这个基本问题,注重贪赃受贿和玩忽职守之罪。秦律《法律问答》规定:“府中公金钱私贷用之,与盗同法。”即私自借用公款与盗窃同论。如果是官吏行贿受贿,则“通一钱者,黥为旦罪”。也就是官吏行贿一钱,要受黥脸而旦起治城的徒刑。对于官吏玩忽职守,法律规定的也相当详尽,稍有渎职失职,就会获罪受罚。
秦朝以降,历代封建王朝关于倡廉笃勤的法律日益详备,形成一个相互协调配套的体系。特别是起源于御史官职的监察制度的确立,使封建官吏的考核、督察有了一套相当完备的制度和专门的机构,对选拔贤才,黜革庸吏贪官,督促勤政,发挥了重要作用。
汉武帝以“七国之乱”为训,即位伊始,便频频下诏,要求各地荐举“廉吏”,其标准就包括清廉与勤政,在他手定的刺察“六条”中,刺察的重点便是官吏的渎职行为。魏晋时以九品中制选官,虽然以门阀为重,但仍然重视廉与勤,将“洁身劳谦”作为选官的重要标准。到了唐代,对官吏廉勤的督查考核更加制度化。
《唐律》规定:监临官吏属下贿赂,受赃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处绞刑;受赃不枉法处刑较轻,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行贿者则“坐赃论减三等”。这样区别情节,不同对待,便于执行和操作。唐代为督励勤政,对流外之官吏实行“四等第考课法”,列为首条的就是“清谨勤公”。唐太宗时,不但委派朝中官员担任黜陟大使,代表皇帝分巡诸道,“察长吏贤不肖,问民间疾苦”,还下诏书令“房玄龄,王珪掌内外官考”,“凡百司之长,岁校其属功过,差以九等”,官吏一旦被列为九等,就被清洗罢免甚至依法治罪。
李世民对州县之官直接临民、与民休戚与共最为关切,特地把地方州府都督、刺史之名写在屏风上,“坐卧视之,得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正是由于唐太宗注重廉勤制度,澄清吏治官场,才有效地促进贞观之治,出现了封建社会发展史上少有的省官简政局面。
据《通典·职官一》记载,“贞观六年,大省内官,凡文武定员六百二十有二而已”,把中央各官府的官员精简掉三分之二。到了宋代,宋真宗所制定的专门用于专核监督官吏的《州县三课》,也是将“公勤廉干”列为首条。
通观这些倡廉笃勤的法律措施,既有对于官吏是否忠诚、效力于朝廷的定性考核;又有对官吏所管辖区域的户口、垦田、钱粮、治安等情况的定量稽查,责任明确,要求具体,规定详备,做到受事有程式,办事有依据,下级工作有准绳,上级检查有尺度。因而封建官僚机构尽管迟暮腐朽,贪墨成风,但廉洁勤政而名重一时的官吏几乎历代都有,更因廉勤并举而受到世人的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