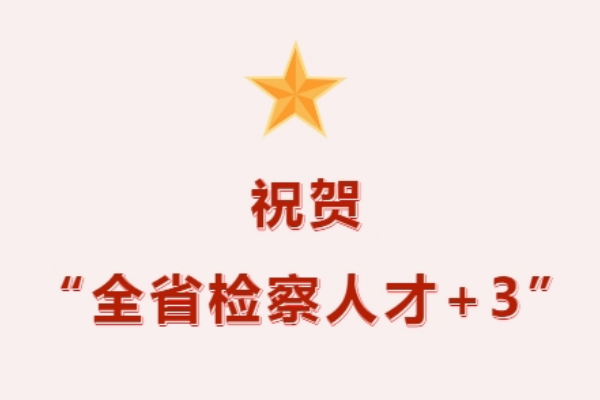法律需求的逻辑性自不待言,缺乏逻辑性的法律如同百合无心、一盘散沙,失去其存在之基石。那么,法律对语言的需求性如何?它所需要的语言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呢?且听作者娓娓道来。
法律是什么?相信初识此题者可以给出诸种不同的答案,譬如,法律是一种社会规范、一种意志表现、一种权衡标准、一种理性体现、一种合同契约……,不一而足。法学界有学者甚至将法律与“修身”联为一体,视之为“君子学道则爱人”式“为己之学”。当然,这些观点感知评议法律的出发点各有不同,皆有其本身的正确性,但是,它们的共同点在于显而易见地遮蔽或忽视了法律自身的语言学特质,换句话说,毋宁法律自身的精妙性、独到性如何,它都需要通过语言(语言的文字转化形式)的载体来呈现给读者并流传下来,并在炼词达意的基础上形诸为法律文本、法律著作、法律活动等法律的语言学表达范式。就此而言,法律的确是一门精妙的语言艺术。
近日,有幸品读了法学随笔文集《法边馀墨》,其中的《时代的法学导师》文章中记述了作者与时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江平先生的师学情谊。提及江平先生的法学课堂,作者绘之为“两千多年前的历史典故和精妙学说仿佛一条精神的河水在课堂之上款款流动”,以至于发出“在一定程度上,法学不正是一门修辞的艺术么”的由衷慨叹!在我看来,“修辞的艺术”也即是“语言的艺术”,作者所意图表达的绝非浅显止于法律需要语言来阐释和播撒本身,而是法律需要与语言真诚地融为一体以实现“灵魂的升华”,是让每一个听众读者都能从传授者的语言中感受并认知到法律的内在思想灵魂,并在逻辑的缜密构架下使人深刻洞见法律的本我与理性。也只有这样,法律才能通过智识的精英们之语言或著作被人们实实在在地感知、了解,成为社会大众的行为准则,而非少数人擘画与讨论的山川之玄和空泛存在。也即是说,法与语言、逻辑须臾不可分离。法律需求的逻辑性自不待言,缺乏逻辑性的法律如同百合无心、一盘散沙,失去其存在之基石。那么,法律对语言的需求性如何?它所需要的语言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呢?
这令笔者想起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一句话:人居住在语言的寓所中。籍此,语言自身的魅力又是如何呢?或许,法国诗人让·彼浩勒的故事可以让我们略窥一二。有一天,让·彼浩勒经过巴黎街头一位双目失明、衣衫褴褛的乞讨老人身旁,老人身旁的一块木牌上写着“我什么也看不见”,向路人诉说着自己身为盲人的悲惨境遇。然而,多数经过老人身旁的行人都无动于衷,老人只能自叹自怨却毫无办法。看到这一场景,诗人在老人的牌子上略做文字改动,将原先直抒胸臆的“我什么也看不见”改成“春天到了,可是我什么也看不见”,很快,奇迹出现了,被修改后文字所巧妙渗漏出的悲伤情愫感染,路人深淀心底的悲悯之心悄然升起,他们纷纷慷慨解囊资助这位失明老人。这个故事向我们折射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精妙的语言之于行为本身并非仅处于依附性地位,它可以通过采摭文字、话语中蕴藏的巨大潜能,精准表达出行为人的思维路径,让受众更易感受思想讯息,以致产生拉近人心的“磁铁效应”。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正是活在自己的语言之中,语言恰如人“存在的家”。
同样,法律作为一种与人类和社会相伴共生的存在,亦如海德格尔的论断,法律也是居住在语言的寓所之中,精妙的语言为法律本我的存在提供了动力强大的支援性论据,促使其与时俱进地生成、存在和演化。在我看来,正是语言与逻辑的演证成就了法律的躯体,失去了语言为载体的法律如同“一个人被孤零零地抛在黑暗里”,缺乏传承的希望。从法律适用语言的标准方面看,法律需要的语言应该是一种大众的语言,生活的语言,甚至可以是艺术的、诗性的语言。
法律语言的大众性意味着这一语言范式必须是社会公众可接受的、可理解的样态,任何出于“拒绝庸俗”目的而将法律语言拔高到晦涩难懂境地的做法都是不科学和不负责任的,这将使法律语言变成少数人的语言,纳入小部分人的圈子,不异于人为筑造起一座分明彼此的“比利牛斯山”,山的这边是大众语言,山的另一边是法律语言,法律因失去智慧的美丽而陷于自毁自弃的泥沼,纵然论述再高屋建瓴,对听者而言仍是“两眼如盲”,只是像诗人海涅嘲弄的那样“播下龙种、收获跳蚤”。著名法律语言学家大卫·梅林科夫在他的《法律的语言》一书中也反复强调法律语言需遵从于大众属性的必要,他认为,法律语言要有价值,不仅要表达思想,而且要承载思想,只有在“独树一帜”理由的支撑下,才可以不使用普通语言,若是缺乏这种理由而偏离普通语言,“特殊的语言”就令人怀疑,就应该以最快的速度予以摒弃。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强调法律语言的大众性,并非片面强调法律语言对于社会公众需具有“可理解”“可掌握”的粗浅特质,它也需要克服大众语言的情绪化、理想化、琐碎化缺陷,将大众语言中背离理性的驳杂成分予以剔除,以免法律语言演进为情绪化的判断与思考,坠入妄言妄思的危端。
法律语言的生活性则要求阐述叙说法律要义的字词、语句必须来源于生活、植根于现实,是一种生活中常用语言的集合体,每一个专业字词都能从日常生活中窥见其原形或现象依据,法律从生活中获得语言的务实性品格,变得富有卓识睿见。正如法国启蒙时期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言,“法律用语对每个人都能唤起同样的观念”,社会公众建立在日常生活经验基础上对它的常规理解应该是同一的。曾经在专栏作家冯象先生《政法笔记》一书中看到,法国杜米耶《法庭辩论》中关于“公庭惶悚之下、言辞每多失措”的插图,图中的一方拍案而起、言语混乱,处于“失措”状态,另一方泰然处之、淡然应对。在冯象先生看来,造成出现“失措”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中一方对“法律文本文字艰涩、案例学说每每自相矛盾”的无所适从,是对非来源于生活中的专业字词的无法把握,以至于笨嘴拙舌、恼羞成怒。在我看来,这也是忽视法律语言的生活性特质带来的尴尬,处于这一情境下的法律语言已变成少见寡闻式遣词造句和云端空谈,尤如干瘪的种子播撒到贫瘠的土地上,因“语言错位”而结不出果实。
法律语言的艺术性乃是法律跃出传统范式桎梏的有益尝试,它揭露了一个事实,即法律也可以在语言的寓所里“诗意地栖居”,可以是“你我都如流水”,而不仅仅是干燥地存在。这也可以看作是“法律与文字”的一次联姻,法律通过文学的语言修饰,将自身严肃谨慎的一面与渊博翩跹的一面融会贯通,避免陷入“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沙漠、一半是绿洲”的角色突兀,是以更优雅的姿态被更多的人去熟悉和了解,实现理性精神的持守与升华。我们可以试想,法律通过语言的载体表现为一种文化的符号,一种理性的诗意,一种规范的哲学,研修法律的人们不仅可以获取对它的理性认知,而且可以获得感性洗礼,这何尝不是一桩美事!
毋庸置疑的是,法律语言范域的准妙适用对于立法、司法环节尤为重要,它是立法、司法者思想花瓣绽放和法治信念播撒的雨露甘泉,是以语言的智慧来诠释法律观点的精髓所在,是一个协助推进社会善治的有益过程。然而,法律语言作为大众的、生活的、艺术的语言范式在实践中往往容易被忽略和轻视,以法学论著为例,有些动辄数百万字的“大部头”公布于世,而包含其内的语言更是令读者觉得晦涩难懂,难觅头绪,这样的法律语言实质上与法律的微言大义并无直接关联,除了显见论者自身语言文字功底之深厚外,反而让读者视作者为“教授老儒”,尚未开始研究书中的奥妙竟已拉开了心理距离,这也是一种著述的失败,甚至可以斥为一种陈规陋习。当然,著述宏丰并不代表内容即乏善可陈,潜心钻研的学者大家们的法律长篇巨作持论严谨、炼词修句,法律语言精致生动,读者仍会不厌其长地击节称赞!这样的法律语言在实质上与其自身的语句、篇幅长短已无关系,它是在法律被理性论证和表达的基础上融入了感情色彩和个人体悟,向世人展现的是法律言说者的一种学术态度和创新精神,而不是机械原始地反映成像。这样的法律语言也必将是以一种优雅的状态而存在,可以绵长如舌吻,纤细如诗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