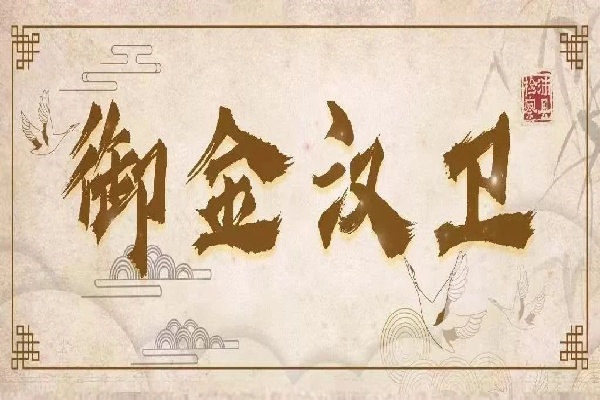江苏省人社厅、江苏省教育厅联合召开全省高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推进会,明确从今年起,下放所有本科院校教师职称系列和实验技术职称系列高、中、初级职称评审权。此次改革变化较大还有评审导向的革新,高校教师职称评价导向不再是原来的“唯论文、唯学历、唯资历”,而是更加突出“师德”。
教师职称一直是一线教师十分关心的话题,高级职称除了事关自己的荣誉之外,还和自己的腰包息息相关。在指标和编制饱和的情况下,很多人为了一个正高和副高指标争得头破血流。这种竞争虽然对年轻研究人员有一定的督促作用,但如果跳一跳仍然够不着挂着的桃子,出现“不评不甘心,参评特累心”的状况,不少人就放弃了。
河南大学对教学不拘一格的重视值得肯定,不过常萍被返聘只能算个案,要纠正大学长期存在的“重科研,轻教学”、“只讲课,不育人”等弊病,不能满足于特例。针对这种现象,今年4月,教育部、中央编办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将职称评审权下放到高校,这也标志着彻底取消行政部门对高校教授和副教授职称评审权的审批管理方式。把职称评审权直接下放至高校,由高校自主评审,是进一步深化职称改革、从体制机制上为人才松绑的必然。据江苏省人社厅副厅长朱从明介绍,新版高校教师职称评价导向会将“师德”摆在高校教师评价的首位,这也是从法律层面上对群众的一种回应,更是对“师德”的一种呼唤。
职称评审权下放,一方面有助于发挥用人主体在职称评审中的主导作用,更加贴近选人用人的实际。济南大学最年轻教授逯一中就是实例。2016年12月,济南大学引进当时刚从国外学成归来的31岁逯一中时,开出的条件直接就是“聘任为教授”。如果按照此前常规晋升渠道,逯一中要先从讲师做起,2年以后评副教授,副教授5年以后才能评得上教授,这还是在科研、教学各方面都比较优秀、晋升过程中一年都不耽误的前提下。
另一方面,职称评审权的下放可以实现高校专业技术评定的分类评价。众所周知,一所高校往往有很多专业,且每个学科性质不同,每位老师的岗位情况也不同,如果是统一评价标准,不利于学科专业的发展和教师岗位的晋升。职称评审权力下放以后,各个高校可以做到具体事情具体分析,自主依法依规评价,这不仅可以促进高校自主创新,将优势学科、特色学科、需求学科做到平衡发展,也有利于教师的培养。从长远看,职称评审权下放也会不断形成并强化“学术共同体”的凝聚力,从而推动高校加快去行政化的步伐。
放权不是一放就灵,在这个问题上,容不得任何简单和乐观。总的来说还存在以下“三个难点”。一是难在与高校行政化正面对峙。高校自行组织评审,本身并无问题,而学校的行政领导多为职称评审主体,如果依然沿袭此前的以行政领导为主体的评价,将“教得好,学生喜欢”的教师拒之门外,则很难完全避免行政化倾向。尤为严重的是,教师迫于现实压力,甚至连申诉的希望都可能会被抑制。
二是难在保障评审的公平公正。笔者认为,职称评审权下放后,学校不仅可以建立以同行专家评审为基础的业内评价机制,还可以引入市场评价和社会评价,对特殊人才通过特殊方式进行评价。对于高校来说,科学分类评价专业技术人才能力素质,避免“一把尺子量到底”,实现“干什么、评什么”。合理合法地制定这些各具特色的评审条件,还需仔细斟酌。
三是难在预防高级职称的泛滥。在目前政策导向下,各个单位似乎都可以自己评审教授等高级职称系列,对于一些落后的地区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但也会产生泡沫,引发高级职称泛滥。大学生,研究生,博士,专家,教授和高级职称都在吹泡过程中和房价一起暴涨,这种变化是改革的需要,但如何顺利解决编制过度问题是个挑战。
可以看到,五年来,本届中央政府工作的“当头炮”都是“简政放权”!此次教育部放权评审职称,可谓顺势“简政放权”而为之。笔者认为,放权举措或需持续“加码”深化,取消职称评审或将成为趋势,取而代之的是提高教师工资待遇和地位,让教师取得实实在在的实惠,真正做到“传道授业解惑”,也给高校松绑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