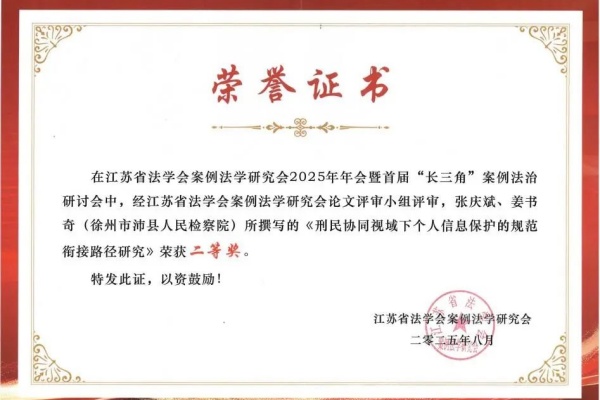刑法结构优化论
——与“严而不厉”和“中罪中刑”两种刑法结构论商榷
摘要
从宏观角度来看,刑法结构是犯罪圈与刑罚投入量的搭配组合形式。在我国刑法学界,围绕刑法结构的最优化模式,有“严而不厉”刑法结构论和“中罪中刑”刑法结构论两种观点。受研究所处的时代和研究视角的限制,上述两种理论均存在不够完善之处。应吸收借鉴其中的合理要素,对我国刑法结构进行优化,科学划定犯罪圈、科学确定刑罚投入量,确保二者之间的组合形式合理、配置均衡。
一、对“严而不厉”刑法结构论与“中罪中刑”刑法结构论的反思
在我国刑法学界,围绕刑法结构的最优化模式,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北京大学教授储槐植提出的“严而不厉”刑法结构论和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卢勤忠倡导的“中罪中刑”刑法结构论。实际上,无论是“严而不厉”刑法结构论,还是“中罪中刑”刑法结构论,均建立在承认我国刑法结构存在犯罪圈划定和刑罚投入量缺陷的基础上。上述两种理论之所以存在明显的区别,不仅因为提出的时代背景不同,而且因为不同论者审视犯罪圈和刑罚投入量的角度有所差异。对此,笔者结合上述两种理论提出的不同背景和视角分别对之进行评析。
对“严而不厉”刑法结构论的反思1
笔者认为,“严而不厉”刑法结构论所提出的以刑罚轻缓作为现行刑法结构的调整方向是不够全面的;调整部分犯罪的法定刑,使其与犯罪属性相适应,达到刑罚适度的程度,同样应当成为未来我国刑法结构调整中“不厉”的内容之一。当然,实现刑罚适度的方法,既可以通过降低部分犯罪法定刑的方式加以实现,也可以将提高部分犯罪的法定刑作为实现手段之一。
此外,应注意到,“严而不厉”刑法结构论仅从宏观视角对犯罪与刑罚的搭配形式进行了较为概括性的描述,而并未真正从犯罪与刑罚之间所具有的互动关系的角度对刑法结构的内部组合形式展开更深层次的分析研究,仅以一个“而”字并不能真正揭示出犯罪圈与刑罚投入量之间的组合形式和搭配关系。
对“中罪中刑”刑法结构论的反思2
从本质上讲,所谓刑事立法之“中”,就是指既不冒进盲目立法,又不滞后懒于修法。审时度势、适度立法才是“中”之根本。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中罪中刑”刑法结构论所提出的“中犯罪圈”的观点与“严而不厉”刑法结构论所倡导的在“法网严密”的思想指导下扩大犯罪圈的做法实际上并不矛盾。更进一步而言,二者均蕴含着法网的设定应当适度的精神,并相应地排斥盲目扩张犯罪圈的做法。只不过在构建相关理论时,“中罪中刑”刑法结构论是以我国1997年刑法修订过程中存在的不合理的犯罪化问题作为研究视角展开讨论的,而“严而不厉”刑法结构论是将我国现行刑法立法存在法网不够严密的问题作为立论基础展开研究的。研究视角的不同决定了由两种理论得出的结论并不相同。此外,严密刑事法网、扩大犯罪圈虽是为了满足预防犯罪和打击犯罪的需要,但这并不一定必然会对刑法所具有的保障人权功能造成损害。只要某种入罪化的处理是必需且适度的,就应当认为,其与刑法所应发挥的保障人权的功能并不存在冲突。否则,如果只要是入罪就被视为侵犯刑法人权保障功能的话,那么,整部刑事立法将会沦为一部彻彻底底的公民人权损害法。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笔者并不赞同“中罪中刑”刑法结构论对“严而不厉”刑法结构论所提出的严密刑事法网、扩大犯罪圈观点所进行的批判,同时,笔者亦认为其所倡导的构建“中犯罪圈”的理念缺乏客观、明确的评断标准,但笔者十分赞同该理论对“严而不厉”刑法结构论中"不厉"的含义进行的反思。
时至今日,以我国现行刑法结构为基础,结合当今世界各国所采取的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和我国贯彻执行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刑罚的轻缓化只能反映未来我国刑法结构调整的一个方面;在排斥总体上重刑结构的前提下,同样应当允许在个罪中采用重刑对犯罪加以惩罚。总体而言,只要法定刑的配置与犯罪的属性是相适应的,就应当认为,该种刑罚投入就是“适中”的。
综合上述分析,无论是“严而不厉”刑法结构论,还是“中罪中刑”刑法结构论,其均以我国刑法结构在犯罪圈和刑罚投入量方面存在的问题为基础展开分析研究,并就此提出了未来我国刑法结构优化的总体方向。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其均存在着合理之处,却又因研究时代的局限性或是受研究角度所限,而具有不够完善之处。
二、我国刑法结构优化的路径选择
结构是组合成整体的各要素间的联结及其搭配组合形式。若要构建一个组织形式合理、实际运行顺畅的刑法结构,就要确保其内部组成要素合理、搭配均衡。从宏观角度来看,刑法结构之优劣与其构成要素即犯罪圈和刑罚投入量密切相关。吸收借鉴“严而不厉”刑法结构论和“中罪中刑”刑法结构论中的合理要素,笔者认为,就我国刑法结构的优化而言,应当确保在科学划定犯罪圈、确定刑罚投入量的同时,进一步权衡犯罪圈的大小与刑罚投入量的配比,保证刑法结构在内部组成上满足要素合理、配置均衡的要求。
犯罪圈的优化1
我国现行犯罪圈基本形成于1997年,发展至今尚不足20年时间,仍然保持了较强的时代特色,且颇具活力。与一些颁行年代较为久远、已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面临着全面推陈出新的域外刑法典相比,我国现行犯罪圈存在的主要问题依然根植于设定之初其自身就存在的缺陷之中。这就是,因固守一元化的“大而全”的刑法典式的立法模式,同时采取特殊的“立法定性+立法定量”的犯罪设定模式,而直接造成的犯罪圈的范围过于狭窄的问题。因此,犯罪化不足是我国现行犯罪圈改造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
当然,着重对犯罪圈进行犯罪化的改造,并不意味着就要放松其中应予推进的非犯罪化的进程。我国现行犯罪圈虽然不存在部分西方国家所面临的伦理道德性犯罪过多和违警罪范围过于宽泛的问题,但其中仍然包含着部分本不应纳入犯罪圈,或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政策的变化其犯罪性已经消失殆尽的行为。对这些行为进行筛选和剔除,是未来我国犯罪圈改造中进行非犯罪化的主要内容。
总而言之,就我国犯罪圈的优化而言,应以犯罪化为主,非犯罪化为辅,确立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并行的调整模式。
刑罚投入量的优化2
从总体而言,我国现行刑法典存在刑罚设置过于严苛、刑罚投入总量过大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死刑和自由刑的大量适用上。对此,“严而不厉”刑法结构论者认为,应将刑罚轻缓作为我国刑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如上文所述,笔者对此持保留态度。不容否认,伴随着人权事业的层层推进和人权观念的逐步深入人心,刑罚轻缓化必将成为我国刑罚发展的方向之一。以对刑罚结构加以轻缓化改造的方法可以解决我国现行刑罚结构中存在的投入总量过大的问题。尽管如此,也不宜将单纯的刑罚轻缓化作为我国刑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刑法结构的构建不仅与罪刑关系、刑法观、立法技术等因素相互关联,更与刑法系统所处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以现阶段我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和法治现状加以观之,单纯地强调刑罚之轻缓,将无助于对频发的新型犯罪和恶性犯罪进行及时、有效的惩治。当然,即便将目光放诸未来,待我国迈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之后,从刑罚结构宏观构建的角度来看,刑罚轻缓化的理念也难以涵盖对轻重不同的犯罪加以区别对待的刑罚配置的全部内容。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将刑罚适度作为未来刑罚投入量优化的方向。
具体而言,在刑种的配置上,应削减乃至废止死刑的适用,并设置多元化的刑罚种类,改变我国现行刑法中刑罚种类设置普遍偏重的局面;在法定刑幅度的设置上,应解决现行刑法所存在的刑种跨度过大的问题,同时要统一规划不同犯罪间的基本犯或加重犯的法定刑幅度;在具体犯罪的刑罚配置上,应调整现行刑法中同罪异罚、异罪同罚和刑罚畸轻畸重等不均衡的刑罚配置,建成个罪刑罚适中、类罪刑罚均衡、异罪刑罚相互区别的刑罚配置体系。
犯罪圈与刑罚投入量搭配组合的优化3
犯罪圈的大小与刑罚投入量的多少之间的配置不够均衡是我国现行刑法结构的一大缺陷。究其原因,既有宏观上欠缺对犯罪圈与刑罚投入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总体性把握的因素,又受具体立法时对犯罪圈与刑罚投入量的对应范围、犯罪圈的大小与刑罚投入量的多少之间的配置关注度不足的影响。针对这一问题,未来在对我国刑法结构进行优化配置的过程中,应当站在刑法结构的高度,重新审视犯罪圈与刑罚投入量的关系。在具体调整犯罪圈与刑罚投入量的组合形式和搭配方式时,应当确立均衡性的基本原则,并从以下三点加以完善:一是保持犯罪圈与刑罚圈的基本平衡,以增加非刑罚处罚措施等方式设置略小于犯罪圈范围的刑罚圈。二是维系罪质与刑质之间的基本平衡,根据犯罪的性质为之搭配性质相当的刑罚种类。三是保持罪量与刑量之间的基本平衡,确保等量之罪配置等量之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