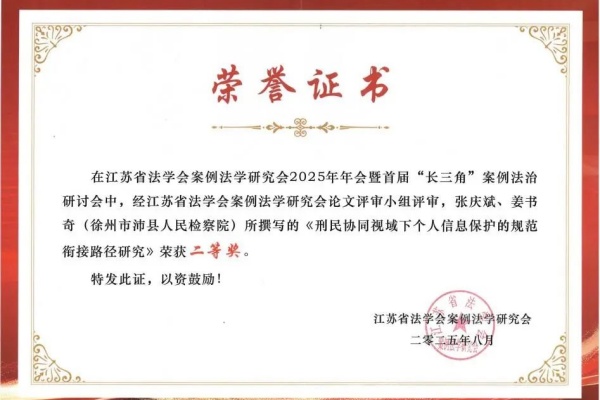最大诚信(Utmost Good Faith)作为英国海上保险法的标志性内容之一,百年来一直被大多数普通法国家的保险法所遵从,甚至被许多大陆法系国家所借鉴。我国海商法中“海上保险合同”一章,在立法之初即深受英国保险法的影响,学界对最大诚信的研究和讨论也从未间断,既不乏对最大诚信的批评,也有认为应当继续秉持最大诚信,并使之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经济条件的观点。从司法实践看,“最大诚信”问题同样无法回避:一方面,从对“中国裁判文书网”2007至2017年的司法案件统计结果看,司法实践中涉及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的主张或认定的判例达到1654件之多,其中“最大诚信原则是保险合同的基本原则”和“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的合同”这两种表述最具代表性;另一方面,“最大诚信”适用的法律后果却相当模糊。原交通部作为海商法的起草单位,曾在2000年委托软科学研究项目对海商法的修订进行研究,其研究报告建议引入最大诚信原则,并规定违反最大诚信原则的法律后果是“另一方有权宣告合同无效”。2014年,交通运输部再次委托软科学研究项目对海商法修订进行理论研究,期间正值英国法律委员会通过2015年保险法对1906年海上保险法(MIA1906)中的最大诚信作出改革。尽管软科学研究项目报告提及英国2015年保险法中“最大诚信” 的改革将对我国海商法中的告知义务产生影响,但没有对其后果以及理由作专门的阐述。2017年6月,我国海商法修订工作正式启动,有关海商法中诚信义务的法律思想、制度内涵及比较法借鉴再次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需要在这次修法研究中重新进行解读和回应。
1
英国保险立法中最大诚信的历史解读
(一)最大诚信的来源
最大诚信似乎是专属于保险法领域的概念。从学界对最大诚信的研究路径来看,英国海上保险法往往是解读最大诚信之含义的源点。英国海上保险法下的最大诚信,以其1906年海上保险法为分界,有不同的含义。
在成文法之前的判例法阶段,通常认为1766年的Carter v. Boehm案是最大诚信的起源。该案当时的大背景是保险业非常稚嫩,保险单的签发只在劳氏咖啡馆通过协商进行,所以曼斯菲尔德勋爵认为,保险的诸多风险大多数只有被保险人知道,保险人既无从获知,也不知道该询问何种问题,只能简单地依据被保险人的告知,因此应该要求被保险人承担告知的义务。该义务被后人总结为Utmost Good Faith,并被翻译为“最大诚信”。但实际上,该案判决本身并没有使用“最大诚信” 一语。依据现有的资料,从字面上看,“最大诚信”的表述最早出现在1789年与保险利益有关的Wolff v. Horncastle案中,但仅是一句话简单地提及“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Contract Uberrimae Fidei),主审法官并未进一步说明什么是最大诚信或者这一概念的渊源,甚至在本案中也并未引用前述Carter v. Boehm案。也有文献指出,关于最大诚信的早期判例也包括普通法院审理的Seaman v. Fonereau案和衡平法院审理的De Costa v. Scandret案。这两个案件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都是关于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告知义务,只不过法官在判决书中未提及最大诚信或者诚信。
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使用了“最大诚信”这一表述,但对于该表述的起源,英国学界始终无法给出确切的回答。“拉丁文uberrimae fidei的用语同样也是较晚才引入的。研究表明,这个词的使用是受到了查士丁尼法典第四卷中有关合伙合同的类似用语的启发。最可接受的观点似乎是这个词并不为罗马法所知,在罗马法中也没有相同的概念。”英国学者霍华德博尼特(Howard Bennett)在2016年南安普敦召开的中英海商法会议上的发言谈到,曼斯菲尔德勋爵在Carter v. Boehm案中是受到了大陆法系尤其是法国法下的诚信原则的影响。在1985年南非上诉法院审理的Mutualand Federal Insurance Co.Ltd. v. Oudtshoorn Municipality案中,罗伯法官在查找罗马法和荷兰法的渊源的基础上指出,罗马人熟知“bona fides”和“mala fides”,但从未将“uberrimae fidei”作为另一种诚信。在罗马法和荷兰法中找不到任何渊源能够支持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这一命题,但其无疑是诚信的合同。对此,有观点认为,“uberrimae fidei”这个词在罗马法中根本就不为人所知——既不是作为独立的法律标准而存在,与“bona fides”也具有差异。更有甚者,“uberrimae fidei”这个词也不为大陆法系学者所知,它只不过是对英国法院和19世纪法律著作中“greatest good faith”的便捷翻译。可以说,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中的最大诚信的含义从该法律术语本身无法找到肯定的答案,还需要从具体法律条文和相关判例中解读。
(二) 最大诚信义务的边界与内涵
英国法下最大诚信义务的边界与内涵的确定过程,实际上是对英国判例法关于1906年海上保险法下最大诚信义务的诠释以及英国2015年保险法改革的全面总结。
从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的条文本身看,其第17条并未尝试对“最大诚信” 给出定义。当然,站在客观立场的学者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立法缺陷:诚信是一个弹性的、不断发展的概念,其更体现为一种态度、一种观点,而不是一个字典上的概念。如果结合案例法揭示最大诚信的含义,则应该从合同前的告知义务入手,因为二者的联系从历史上看最为密切:Carter v. Boehm案关于诚信义务的判决主要涉及告知义务和误述,这使得此后立法以及案例中关于最大诚信的讨论几乎皆围绕告知义务和误述展开。但最大诚信义务在英国法下显然并不局限于合同前的告知义务。
1.最大诚信与欺诈索赔
Carter v. Boehm案主要关注的是保险合同订立前的最大诚信义务,并曾引起最大诚信义务是否仅仅适用于保险合同订立之前的争论。但是,自19世纪的Britton v. Royal Insurance Co案开始,英国法院就判定,如果有人欺诈性地夸大其索赔,则其全部索赔将被没收,而不是仅仅拒绝赔偿夸大的部分。法院认为,如果允许当事人去尝试这种欺诈是非常危险的。应该说,该“没收规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此后,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中欺诈性索赔将导致“合同被另一方宣告无效”的大原则与之并不一致。在之后的英国判例法中,隆摩尔法官在The Mercandian Continent案中具体列举了合同订立后最大诚信义务适用的情形,其中一项便是“欺诈性索赔”。在The Star Sea案中,英国上议院还在两个方面限制了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17条的适用范围:(1)一旦法律程序开始,最大诚信义务就不再适用,而应该适用法院程序。(2)合同前诚信义务与合同后诚信义务有所不同,合同前义务相对比较严格。由此,欺诈性索赔中的诉请及证据采信标准就不再适用“违反则对方有权宣告无效”的最大诚信义务规则。不过,此后英国司法实践在执行该案所确立的原则时,又出现了观点的反复和演进。在The Aegeon(No 1)案中,曼斯法官认为,欺诈性索赔受普通法规则调整,而非受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17条的调整。因此,当发生欺性索赔时,保险人不得宣告合同无效。理论界也有不同的观点:英国保险法权威著作《麦吉利夫雷论保险法》一书作者认为,“没收规则”和“宣告合同无效规则”可由保险人在抗辩时选择适用;但克拉克(Clarke)教授则认为,“应该只有一种理论:欺诈性索赔全部不应支持,且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但之前的诚实索赔继续有效,且保险人不能要回其他索赔已经赔付的款项”。在Axa General Insurance Ltd v. Gottlieb案中,曼斯法官显然支持了克拉克教授的观点,并再次申明欺诈性索赔受特别的普通法规则调整。在该案中,尽管被保险人存在欺诈性索赔,但保险人仅可免除其对欺诈性索赔部分的赔偿责任,而之前的诚实索赔则继续有效。总结来看,近几年英国的主流观点在发生转变:欺诈性索赔不再受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17条中的“一方宣告合同无效规则”的调整。
2.最大诚信对保险人的适用
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17条显然还有一层含义:最大诚信义务不仅由被保险人承担,也应由保险人承担。保险人的最大诚信义务主要表现为:(1)对承保风险的告知义务,即如果保险人得知保险标的已经不可能因发生保险事故而遭受损失的,应将该情况告知被保险人;如果保险人知道被保险人所期待投保的风险其实并不在保险单的承保范围之内,则也应如实告知保险人。(2)对保险合同条款的释明义务,即保险人应当向被保险人说明合同的内容。(3)及时支付保险赔偿金的义务。最大诚信适用于保险人是明确的,但是保险人违反最大诚信义务后,对于被保险人的救济措施却非常僵硬。从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看,一方违反最大诚信义务,无论该行为发生于合同订立前还是订立后,另一方唯一的救济方式就是宣告合同无效。据此,另一方不得援引合同法下的其他救济方式,如主张损害赔偿。这种救济措施显然存在明显的不合理之处。在Banque Keyser Ullman S.A. v. Skandia(U.K.)Insurance Co Ltd案中,保险人明知被保险人的代理人故意向被保险人隐瞒保险合同的部分条款,却未将上述情况告知被保险人,一审法院认为保险人违反最大诚信义务且被保险人有权向其主张损害赔偿。上诉法院维持了一审法院关于保险人违反最大诚信义务的判决,但推翻了被保险人有权获得损害赔偿的裁定,这一判决也得到了枢密院的支持。由此,保险人违反最大诚信的后果却是被保险人得不到保险赔偿。在前述The Star Sea案中,霍布豪斯勋爵同样认为,一方违反最大诚信义务时,另一方可以溯及既往地宣告合同全部无效。如果因此需要对双方的经济地位进行调整,依据的是返还法(restitution law),而不是合同法。很显然,宣告合同无效仅在保险事故尚未发生时才对被保险人有意义,其本身并不能满足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的救济诉求。但被保险人往往要等到保险事故发生时才能发现保险人未尽最大诚信义务,在此情况下,即使被保险人得知保险人违反最大诚信义务,也几乎不会因此宣告合同自始无效,故宣告合同无效的救济方式在多数情况下对被保险人并无实益。为弥补此种不足,英国2015年保险法在第四部分特别针对保险人的迟延赔付行为,创设了对被保险人的救济机制——对及时支付保险赔偿默示义务的确认。在英国法下,一旦该义务成为默示条款,则意味着其将与合同中其他明示的条款一样可以适用普通法的违约救济。这改变了过往英国判例法认为保险人及时支付保险赔款不构成保险合同下默示义务的传统。此外,保险人违反有关风险告知与条款解释说明的义务时,英国的司法实践对被保险人的救济也很少见到基于合同被一方宣告无效而否认被保险人的赔偿请求权的情况。
3.最大诚信在合同订立前后的差异性
英国上议院在The Star Sea案中明确了最大诚信不仅可适用于保险合同订立前,还可适用于保险合同订立后。该案中,在保险合同订立后,保险人发现被保险人未告知其所有的另一艘配置相同的Kastora轮由于同样的设施起火而造成全损的事实。该案同时明确了最大诚信在合同不同阶段的义务标准是不同的。对此,克莱德勋爵在该案中作出如下解释:“保险合同中的诚信理念反映了对当事人告知义务的要求,但该要求并非一成不变。该义务的内容随着合同的履行而变化,需要通过法院的裁判来确定。在合同订立阶段要求非常高的公开程度是合理的,但合同成立后,仍要求同等的程度则不具有正当性。” 该解释的逻辑是:若这种义务完全相同,则被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后违反最大诚信义务的,保险人即可宣告合同无效。其不仅可以免除向被保险人支付本次事故保险金的责任,还可宣告保险合同自始无效,向被保险人主张返还之前赔付的保险金,即使这些保险金的取得完全合法有效。这种违反后果的严厉性虽会对被保险人起到阻吓作用,但其不公平之处也非常明显。正因为此,英国法院在一系列案件中对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17条的适用范围进行了限缩性解释。在The Mercandian Continent案中,隆摩尔法官认为该法条的适用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1)被保险人的行为对于谨慎的保险人评估风险至关重要,且足以诱导保险人作出不同的意思表示,即被保险人的违约行为须同时满足实质性和诱导性两个标准。因此,被保险人的违约行为应与保险人的最终责任有关系,或者至少与保险人的抗辩有关系。(2) 被保险人的违约行为相当于毁约(repudiation of the contract),因为宣告合同无效比毁约的救济方式更为严厉。此先例确立后,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17条的解释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使不是不可能,最大诚信也将很难适用于保险合同订立后”。
4.英国2015年保险法改革
在2015年保险法之前,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除了一些特殊制度规则(如默示条款、推定全损) 外,总体上适用于普通商业保险,而非商业保险(即消费者保险) 适用英国消费者保险法(Consumer Insurance(Disclosure and Representations)Act 2012,CIDRA)。另外,汽车保险中的强制责任保险、普通责任保险、雇主责任保险和人身意外险等特定保险领域也有相应的法律调整。在此情况下,尽管英国判例法已经对1906年海上保险法有所发展,英国法律委员会仍决心通过新的保险立法对最大诚信进行改革。2015年保险法出台之后,1906年海上保险法的部分条文已经被替代,其他部分因不存在明显的适用冲突将继续有效。
首先,英国2015年保险法在第五部分“诚信”中,对违反诚信义务的法律后果进行了修改。该部分标题使用“诚信”(Good Faith),但内容却是围绕最大诚信展开。其第1条规定,违反最大诚信义务的后果不再是宣告合同无效。其第2条进一步规定,任何有关规定保险合同为最大诚信合同的法律规则,应该修改为以该法以及消费者保险法所要求的程度为限。其法律效果是:消费者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的告知义务和陈述义务为“不作误述的合理注意义务”;针对具有海上保险属性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如私人游艇保险合同) 下的最大诚信义务,消费者保险法将优先于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17条适用。因此,最大诚信义务的具体边界在英国2015年保险法第五部分中没有涉及,而是要参照该法其他部分的规定以及消费者保险法的相关规定。至此,最大诚信在英国保险法下依然存在,但成为一项具有指导功能的解释性原则(interpretative principle)。
其次,该法将诚信义务具体化,分别对告知义务、保证、欺诈性索赔及迟延赔付进行了具体规定。值得注意的是,该法在第二部分引入了“公平陈述”(fair presentation)的新模式来代替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18条、第19条和第20条中的告知和陈述义务模式。这实际上融合了传统的告知义务及陈述两项内容。该部分将告知义务的标准修改为“有限的主动告知义务”(limited disclosure):如果被保险人不能达到“无限主动告知” 的要求,“被保险人也应告知保险人充分的信息,以使谨慎的保险人能注意到其需要进一步询问被保险人以揭示这些重要情况”。同时,该法将投保人(proposer)违反告知义务或陈述义务的特定违约(qualifying breach)区分为故意、重大过失和其他违反两种情形来详细规定。对于前者,其救济是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对于后者,救济则要视假如保险人知悉被保险人公平陈述的信息的反应而定:(1)宣告合同无效:如果保险人会拒绝承保,则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但须归还保费;(2)选择赔付:如果保险人会选择某些事项承保,则保险人仅承担其可能承保事项的赔付义务;(3)比例赔付:如果保险人会增加保费,则保险人按照实际收取的保费和可能收取的较高数额保费的比例进行赔付。
5.最大诚信的内涵总结
综上所述,在2015年保险法之后,英国法下最大诚信义务的边界已经扩展到被保险人的告知义务、陈述义务、保证、不欺诈性索赔和保险人对保险条款的说明、不迟延赔付以及弃权和禁止翻供等领域,其特征也变得非常具有典型性:第一,在普通合同法的陈述义务之外加设有限的主动告知义务。第二,即使是有限的主动告知义务,主动告知的本质并未改变,仍是对传统的合同法下“买者后果自负”(caveat emptor)原则的颠覆。也就是说,在保险法下,被保险人在谈判合同时应谨慎地选择哪些信息应向保险人披露,保险合同谈判阶段的诚信义务标准仍然高于普通合同。第三,在合同履行阶段,合同方履行义务要诚实、公开和坦白(candid),当然诚信的具体要求因时代的不同其内容也有不同的解释。第四,抽象的最大诚信被具体化,违反诚信的救济方式也由单一的规则演变为各种个性化的救济途径。
2
诚信与最大诚信的关系考察
可以观察到的是,2015年之前英国保险法的案例主要是围绕某项义务的违反是否适用海上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而展开争论,并没有回答最大诚信与合同法下的诚信有何分野。2015年之后英国保险法将最大诚信义务修订为一项解释性的“原则”,实际上是对保险法诚信理念的较大改变。自此,英国保险法下的最大诚信与合同法下的诚信原则也将不可避免地产生纠缠。就我国而言,我国保险法已秉承大陆法系传统确立了诚信原则,而且根据一般法与特别法的适用规则,该原则同样适用于海上保险。我国海商法的修订是否以及如何借鉴英国保险法下的最大诚信,也必须以厘清诚信原则和最大诚信的关系为前提。
(一) 大陆法下的诚信
诚信概念源于罗马法,主要作为程式诉讼中的特殊条款——“欺诈例外”(exceptio doli)而发挥作用。但随着程式诉讼的式微和最终废除,诚信概念为更宽泛的公平(aequitas)概念所吸收。在整个中世纪和现代社会早期,诚信和(或)公平也支配着商人之间的关系,成为商人法的基本原则。大陆法系显然继承了这一原则。德国民法典在第二编债的关系法中规定了债务人有义务依诚实和信用并参照交易习惯履行给付,并引申出一系列附随义务,如合同前的告知义务和合同后的单证交付义务、协助义务、保护义务和披露义务等;德国民法典还在总则编规定,对合同的解释,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并考虑交易上的习惯。德国保险合同法(2008)中并没有对诚信原则的直接表述,相关内容将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意大利民法典也规定了合同的磋商和订立过程、合同的解释以及合同的履行应遵循诚信,但意大利保险法中并没有关于诚信或善意的表述。法国法除其民法典中关于合同的规定外,其诉讼法、消费法、劳动法和行政法中皆有诚信的要求。合同谈判阶段的诚信原则在法国不仅为法学理论所承认,在当前也被民法典和保险法等法律所承认。诚信在合同磋商、订立和履行阶段都有要求,并被认为关涉公共利益。法国保险法中虽然没有体系化的诚信制度,但有涉及诚信义务的规定:如被保险人违反询问告知义务时,除非被保险人证明其已诚信履行合同,保险人不承担若知道此种信息就拒绝承保的风险;任何导致风险增加的合同修正应当在三日内通知保险人,除非被保险人证明其诚信地履行了合同,否则将承担违反合同的责任。
欧盟法中没有关于保险和再保险合同的订立与履行的统一的一般性规则。兰多委员会草拟的《欧洲合同法原则》明确规定了诚信,并且不允许合同双方约定排除该条文的适用。同时,欧盟不少法律也规定了诚信,要求不仅合同条文要公平合理,而且订约的程序和实体都要公平合理,并且不允许合同排除或者限制诚信规则的适用。这些有关诚信的原则或规则,其效力均由欧盟各成员国内法调整。
可见,大陆法系的合同法中总体上承认并执行一条至上的原则——诚信订约和履约。其含义远远超出“互不欺骗”的标准,而是类似于“公平交易”,旨在通过诚信原则对合同订立以及履行中的不公平情形进行矫正。部分国家如法国、德国、瑞士和奥地利等的合同法或保险合同法对谈判阶段的义务要求设定较高,要求每一方谈判时尽量考虑对方的利益,并根据当时的情况提供适当的信息和建议。但是,这些国家的保险法中并未直接使用“最大诚信”的概念。
(二) 普通法下的诚信
罗马法下的诚信原则显然并未被英国法所接受,英国法也未接受当代欧盟法中的诚信原则,而是发展出解决公平问题的“碎片化方案”(piecemeal solution)。多数英国学者认为,英国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诚信原则。其原因主要有三:第一,英国法用碎片化的个案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采用广泛使用的大原则。第二,英国法代表了自由主义的社会思潮,合同方有权利在合同中追求自己的利益。第三,鉴于诚信内容的模糊性与主观性,承认诚信原则令人担心会产生太多的不确定性,而是否破坏合同确定性的目标恰恰是英国法所看重的。英国法下,如果合同方欲以诚信来约束双方的订约谈判或是合作,必须以明示条文来表明此种意愿,否则法院会拒绝执行。整体来说,英国法院更尊重订约自由、当事人自治和严格履约,诚信并不是足以改变合同的理由。例如,航运市场高涨时,租船合同下的船东趁租方未能按照合同及时支付租金行使选择权撤船、终止租约的做法,在英国法下并不会被认为有违诚信。同时,英国法也认为,诚信与承认每一方有权合法地为自己谋取合约下的利益以及谈判双方处于敌对的地位,在法理上有根本的矛盾。此外,诚信往往与“不占对方便宜”“不投机取巧”等道德标准相关,但道德标准难以界定,而且合同一方主观上如何考虑也很难判断。
所以,英国法下仅将部分特殊类型的合同归类为“诚信的合同”,如合伙合同,因为这种合同必须由双方紧密合作才能履行;又如雇佣合同,因为普通法中要求雇主如果没有合理的理由不能破坏合同双方之间的信任。这些具有显著诚信要求的合同被称为“诚信的合同”。对于其他普通合同,英国法院仅在某些领域承认有限度的诚信:第一,对裁量权的承认。行使裁量权的标准就是公平、合理、诚信及不能误解法律。例如租船合同中船长对港口是否安全以及天气状况是否允许开航的判断。第二,英国法院对于商业合同条款中呈现的承认诚信的趋势持开放态度,尤其是标准格式合同中对诚信的规定。例如合同条款要求双方诚信地达成关于公平合理的市场价格的协议或者是合同方以相互信赖和合作的精神来行事等。第三,对诚信默示义务的部分承认。在Yam Sheng案中,法院确认基于合作关系的“诚实意义上的诚信”这一默示义务可以在商业协议中存在。该判例的要旨在2014年被英国法院的数个案件所遵从。第四,对于诚信地谈判条款效力的确认。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法院对商业合同下的合同前诚信义务并没有开放,但对于规定双方诚信地谈判的合同条款或“协议将来达成协议”(agreement to agree)的态度却有所转变:其起初对“协议将来达成协议”的做法并不支持,但随着“互锁协议”(lock-out agreement)等在实践中的应用和现实价值,英国法院也开始承认其有效,但前提条件是合同方必须有订约意图且谈判的期限必须明确。与普通合同相比,英国法下“诚信的合同”要求合同双方在订约阶段即负有主动告知义务,而普通合同并不设有此项义务。而在合同的履行阶段,二者并无显著的差异。
美国《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和《统一商法典》总体上将诚信义务的适用范围限于对已成立合同的履行和执行。但《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在个别合同的订约阶段也要求依诚信履行义务。在澳大利亚法律中,法院很普遍地援引诚信认定“诚信地协商合同”(negotiate contract by good faith)在合同法下的可执行性,并很愿意认可普通合同双方应该在履约时密切配合的默示条款。但澳大利亚1984年海上保险法几乎是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的翻版,该法中的最大诚信义务规定与英国法完全一致。
总体来看,受英国法的影响,普通法下的合同法中虽然有诚信义务的要求,但订约阶段的诚信义务却并不普遍。最大诚信义务则为保险法体系所独有。
(三) 最大诚信与诚信原则的差异
英国法与大陆法系国家的诚信要求既非完全割裂,又存在差异。首先,在英国法下,一旦商业合同被归类为诚信的合同,则表示这些合同与大陆法系下的合同一样,订约和履约过程都受到道德的约束,只不过在订约阶段要披露于己不利的信息,这对商人而言是更高的道德标准。因为诚信意味着须为合同相对方的利益着想,与为己方谋利的商业合同目的相背离。而大陆法系下的诚信原则相对宽松得多,诚信原则并不反对商业合同的当事方谋利,其更多地强调公平、守约与守法的意识,但在订约阶段告知义务的标准并不要求主动告知。其次,对于普通的商业合同,英国法认为在合同履行阶段双方需要进行密切配合和沟通,这与大陆法系下所有合同履行阶段的诚信义务有所趋同。但英国法认为,虽然有的合同应该设定诚信义务,但不宜设立宽泛、不确定的大原则,而是应该设定具体而确定的义务规则。所以,英国法下的诚信义务标准更为明确和严格。大陆法系的诚信原则看似对双方当事人设定了没有上限的诚信要求,甚至可以推断,轻微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也将受到制裁,但司法实践并没有给出充分的例证,反而更看重原则对于法律规则模糊或遗漏之处的补充功能。最后,英国法下的合同解释原则中并不存在诚信原则,一是因为英国普通法没有诚信原则的要求,而是用具体的合同法概念来解决问题(比如误述或禁反言等);二是英国法尊重合同意思自治,权利义务由合同约定,不附加诚信义务。在大陆法系,诚信原则是合同解释的重要原则之一。
特别就保险合同而言,英国法下的保险合同不仅满足上述“诚信的合同”标准,而且在此基础之上使用了“最大诚信”的用语,并设置了违反最大诚信的救济规则以及与最大诚信义务相一致的主动告知义务。而大陆法系下当前并无权威的论著认为保险合同对诚信的要求与其他合同有明显的差异,大陆法系的现有立法一般将对诚信的要求在总则中设为基本原则,然后在分则中设定标准不同的具体诚信义务。虽然这些诚信义务中设定主动告知义务的情形并不多见,但传统航运国家的海上保险法规范中也有不少范例,只不过大陆法系的保险法中难以找到“最大诚信”的提法。在此基础上,弄清英国法体系的保险法与大陆法系的保险法关于诚信的差异,关键在于最大诚信中的“最大”是否有实质的法律含义,以及最大诚信是法律原则还是规则。
英国法下对于最大诚信与诚信是否具有同等含义,确实有过争论。鉴于“最大”诚信的字面含义,其容易被误解为:“在保险合同的各个阶段当事人均需满足最高程度的诚信要求”。但实际上,如前所述,在保险合同的不同阶段,对当事人诚信的程度要求是不尽相同的。对此,英国有学者对于“最大”用词的必要性也产生质疑,认为“最大”一词并没有增加新的含义,甚至是多余的,最大诚信实际就是诚实信用。更有学者认为,“最大”是19世纪立法增加的用词,并非曼斯菲尔德勋爵在1766年Carter v. Boehm案判决中的措辞。可以肯定的是,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中所使用的最大诚信一词,并非经历了从一般诚信到最大诚信的演变过程,没有依据说明最大诚信是诚信的特殊形式,也没有证据支持最大诚信是诚信的更高位阶形态。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就此断定“最大”就是多余的,至少法官在判断合同一方是否违反诚信时,“最大”的要求依然会有鲜明的提示效果:因为此处诚信的要求较高,就不允许合同方轻易违反。因此,“最大”的措辞仅具有更容易促使法官认定违反诚信的条件已然满足的潜在效果,但最大诚信与诚信在实质的法律含义层面并无差异。对此,南非上诉法院罗伯法官更是直接否定了“最大诚信”这一提法的必要性:“最大诚信并不是一个具有准确内涵的法律术语,故不能将其作为具有准确法律意义的标准而予以适用。它是一个外来的、模糊的、误用的表述,其在法律中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的法律不能以最大诚信作为保险合同缔结之前的就重大事实履行告知义务的法律基础。我们的保险法并无保留最大诚信之必要,现在将之予以抛弃适逢其时。”英国法律委员会在起草保险法草案时,也曾经慎重地考虑过,在保险立法中是否还需要将诚信义务表述为最大诚信义务,简单表述为诚信是否足以表达其含义。调查结果显示分歧很大:有人认为这两个概念可以互换,也有人认为“最大”二字至少承担着区别保险合同与普通商业合同的功能。最终,英国2015年保险法依然保持了“最大诚信”的概念,但将本部分的标题确定为“诚信”而非“最大诚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最大诚信与诚信的差异不在于诚信是否“最大”,而在于诚信本身在不同法系和国家中因其缘起与历史演变的差异而形成的被业界普遍接受的不同含义。
至于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下的最大诚信在法律适用上属于规则还是原则,按照当前有关规则与原则的区分标准,最大诚信应是规则。首先,法律规则所具有的“全有或全无”的适用结果,与最大诚信义务存在的依据——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17条所规定的“违反则对方有权宣告合同无效”的单一适用结果完全一致,其不具备法律原则适用时的伸缩性或灵活性。其次,“违反则对方有权宣告合同无效”的条文,同时具备假定条件、行为模式、法律后果三项法律规则的要素,因此具有明确的规范性,而法律原则并不直接包含任何具体的决定,它本身并不一定直接解决问题。基于此,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17条关于“最大诚信义务”的条文当属于法律规则而非法律原则。英国权威海上保险法著作《阿诺德论海上保险法与海损》也使用最大诚信义务的表述,这也是英国诸多权威判例的表述方式。而普遍存在的“最大诚信原则”的说法,主要是因为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的区分是在德沃金于1967年发表“原则理论”之后才获得广泛认同的。在此之前,因为最大诚信义务所呈现的“违反则一方可宣告合同无效”的严厉后果,使得保险合同双方为维系保险合同的效力而谨慎地将最大诚信奉为圭臬,由此一些英国法学者将其称为“原则”。当然,在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进行区分的当代,也有英国法学者在研究最大诚信义务时仍然习惯地不对“原则”和“规则”进行精确的划分。这种情况对国内学者也影响至深,也是国内不少学者认为最大诚信是英国保险法基本原则之一的原因所在。
3
我国海商法中与诚信原则有关的告知义务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英国财政部于2014年7月17日向上议院提交了《保险法法案及其解释报告》,详尽展示了英国法律改革委员会近年来对于最大诚信义务进行改良的具体内容及思路。但是,我国保险法学界及实务界人士却有相当大的比例认为我国保险法或保险业务中已在遵循“最大诚信原则”,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对英国保险法的借鉴研究。因此,在对诚信与最大诚信的关系予以考察之后,需要进一步厘清我国保险法中的诚信原则与当前英国法中的最大诚信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回答我国海商法在修订时对与诚信原则有关的具体义务是否需要作出调整这一重要问题。
(一) 是否引入最大诚信概念
由于没有证据表明英国传统海上保险法下最大诚信义务所具有的功能会导致优质的业务离开伦敦保险市场,且没有一致性意见和决定性论据支持用“诚信” 替代“最大诚信”,使得英国保险法改革时亦未能舍弃“最大诚信”。英国保险法对于最大诚信制度加以改革后,其主要特征在于,一是在法律中明确了最大诚信原则指导性的解释功能,最大诚信在英国法下从规则转变为解释原则,二是强化了合同前和合同后的主要义务并对违约救济途径作出具体规定。英国法的改革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在于:第一,诚信解释性原则与具体化义务和多元化违约救济方式相结合的立法模式缓和了传统上违反最大诚信义务后果的严厉性。第二,最大诚信义务得以尽可能地明确。第三,以诚信解释性原则为未来法律规则可能存在的模糊之处提供指导。
从最大诚信中“最大”含义的澄清以及原则和规则的区分来看,我国保险法中的诚信原则与当前英国法中最大诚信的差异实质上可归纳为:一是,基于法系的不同,我国保险法中将诚信原则作为基本原则及合同解释原则,与英国保险法下将最大诚信作为指导性的解释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具体形成裁判规则方面可能存在差异;二是,有关诚信的告知义务、保证、欺诈性索赔和弃权等具体义务的设定可能不同。在洞察这两点实质差异之后,在我国保险法已秉承大陆法系传统确立了诚信原则的情况下,我国海商法的修改已经没有必要再拘泥于“最大诚信”这个本身极具模糊性的概念,况且就我国海商法或保险法的立法特点而言,也不可能在成文法精炼的法律条文中将“最大诚信”的含义阐释清楚。
我国海商法修法的重点应在于,充分发挥海商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作为特别法的优势,针对关涉诚信的保险合同双方的合同前及合同后义务,在该法中作出与社会形态及科技发展趋势相适应的、对保险合同双方的具体诚信义务进行合理再平衡的明确规定。同时,通过修法和未来的司法解释,将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所通常引用的“最大诚信”概念的内涵逐步统一于通俗易懂的“高标准的诚信要求”的理念之上。
(二) 是否修订告知义务规则
英国保险法在诚信原则之外,规定有关告知义务、欺诈性索赔等具体的诚信义务,并对违反诚信义务的救济用具体的法律规则进行限定。其中,订约阶段告知义务的安排是诚信制度最重要的表征。我国海商法和保险法下的具体告知义务将对我国诚信原则的解释与适用产生最为直接的影响。从比较法的视角来看,出于对消费者保险的考虑,一些国家对告知义务的设定更多是采用“询问告知”模式,而多数的海上保险法或准立法中,则以“主动告知”居多。我国海商法第222条第1款所采取的“主动告知”模式是否需要作出调整,是当前修法研究中必须回答的问题。
质疑主动告知义务的理由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被保险人不比保险人更专业。二是,在数据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保险人比以前易于获得保险标的的信息,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立法之初保险标的的重要信息均由被保险人单方掌握的假设并不成立。三是,被保险人可能并不知道应当告知哪些内容,或应当告知到何种程度,从而导致违反告知义务的“无心之过”。因此,被保险人可能会通过向保险人提供大量未经整理的信息的方式来履行告知义务。例如,将所有相关的信息都刻录到一张光盘上,让保险人自己整理和决定哪些是和风险相关的重要情况。英国法律委员会将上述情形定义为“信息倾倒”。相比之下,保险人显然比被保险人更清楚用以评估风险级别及费率高低的信息类别,但保险人却可能滥用其承保人的地位,在承保时缺乏足够的动机主动提出其关心的与风险有关的问题。
对于主动告知义务的调整首先从英国法院开始。英国有判例认为,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18条中的“主动告知义务”,应受到“弃权”理论的制约。也就是说,如果被保险人给予保险人足够的信息,使得谨慎的保险人有必要对被保险人作出询问,保险人就应该作出此种询问。如果保险人未能做到,就不能以此类信息未能披露为由寻求救济。该判决的合理性在于,保险单持有人虽然掌握事实,但保险人却了解哪些事实相关,为有效完成投保程序,保险人必须承担评估所告知的信息以及进一步询问的角色。基于英国法院前期的判决以及2015年保险法起草过程中对告知义务模式的调研,英国2015年保险法最终对告知义务进行了改变,在第二部分使用7个条文详尽规定了被保险人的“合理陈述义务”(duty of fair presentation)。保险人在被保险人的告知义务的履行方面必须紧密配合:被保险人仍应该将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重要情况如实告知保险人;或者,如果未尽到上述要求,被保险人应告知保险人充分的信息以使谨慎的保险人能注意到其需要进一步询问被保险人以揭示这些重要情况。即采用了“有限度的主动告知义务”的模式。
英国2015年保险法所采模式的实质,是增加了保险人一定限度的询问义务,并以被保险人的“合理查询”义务相平衡。这可以视为“主动告知”和“被动告知”之间的折衷。英国保险改革法案本来不乏反对的声音,但其最终能够在英国议会获得通过,说明保险法改革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大卫哈泽尔(David Hertzell)在立法听证会上关于保险法草案的内在价值取向的阐述说服了议员——“我们这些提案背后所蕴含的理念是要全面提升保险市场参与人的专业化”;也说明英国财政部所指出的修法目的获得了立法议员的认可——“草案的目的是使这些领域(告知和陈述、保证及其他术语以及欺诈性索赔)的成文法框架实现现代化,并使之与现代英国保险市场最好的实务操作相一致”。
英国法律委员会关于告知义务立法的改革可能是成功的,但这并不等于我国海商法或保险法必须借鉴。尽管我国早已是世界上第三大保险市场,但英国保险市场中投保程序的专业化却远非我国能比。表面上,我国保险市场中的投保业务逐渐像英国一样由经纪人、代理或者销售公司来完成,但似乎价格和承保范围等表面环节更受关注,深层次的风险管理和保费精算却在投保程序中严重缺位。因此,英国保险法的改革内容能否适于我国保险市场的实务操作现状,能否促进我国保险市场参与人员的专业化,尚有疑问。
从对“中国裁判文书网”2007-2017年的司法案件统计结果和我国海事法院自2013年起上网的25份有关诚信和告知义务的生效判决的研判结果看,我国司法实践中依诚信原则解释出来的订约阶段的义务标准比英国法宽松。25份生效海事判决中,被保险人按照投保单的内容如实填报相关信息后,保险人认为被保险人未告知相关信息的主张无一获得支持,判决理由主要是保险人未完成举证责任以及保险人作为更专业的一方应该对其认为重要的信息进行询问。也就是说,我国法院对于被保险人是否尽到告知义务的认定标准并不严苛,也不认为保险人可以“坐等”被保险人的无限告知而无任何询问义务。此外,对2017年全国海上保险业务排名靠前的10家保险公司的实践操作环节的调研也表明,以下三个层面的结果值得关注:
1.保险人并非完全等待被保险人的主动告知,也采用询问、沟通和填写问题单的方式来表达对于投保标的信息的关注,形成了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诚信合作。在实务的订约流程中,投保人通常会将投保标的和投保意向等信息通过各种方式发给保险人(核保部门)询价(如招标文件或询价邮件),甚至一些简单的业务仅经口头沟通后便直接投保。保险人接到询价后,在报价之前需审查对其告知的信息是否满意。如果对其中的信息有疑问或需进一步澄清,保险人会询问关于标的风险状况的相关问题。
2.保险人对于告知的要求及标准与被保险人的业务规模以及可信任度存在关联。核保人不仅要管控风险,还要兼顾险种的市场经营,并定期根据盈亏报表调整经营思路。因此,在市场压力下,核保人针对小规模的零担客户报价会比较严格,表现为约定特别条款和比较全面的询问,但是针对平台客户或物流园项目等则仅仅询问年保费规模、出单货物种类等,核保系统会留给保险代理人或相关平台一定的自动核保权限,或采取预约保险协议的形式,不需要被保险人在订约阶段告知较多的信息。
3.调查问卷的使用缘于保险人对于关键风险因素的重点关注。海上保险中的船舶险、物流责任险、码头责任险以及为适应市场而开发的新险种,通常被列为高风险的险种,其核保程序采取传统的、严格的“一船一单一报价”、《客户调查问卷》或《标的风险调查表》的方式,由被保险人申报,再根据申报内容报价,进行相关特别约定。而对于一般的货物保险,其订约阶段的告知或询问程序则相对简化。虽然主观上并非为了减轻被保险人的告知义务,但客观上有助于被保险人履行其告知义务。
从以上对实务操作的调研可知,尽管海商法第222条第1款通常被解读为“无限而主动的告知”,但是保险的实务操作并不存在一个始终由被保险人(投保人) 主动进行无限告知的程序,保险人的询问已经构成投保程序不可或缺的部分。此种主动告知与辅助询问相结合的模式,一方面避免了保险人承保地位的滥用,另一方面也在标的本身的特殊性导致保险人询问不足时,将被保险人的充分告知设置为兜底义务。当前,我国保险人对于被保险人诚信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表示严重关切。从对国内法院公开判决的保险欺诈刑事案件的统计结果看,被保险人的诚信状况依然堪忧,况且尚有数量巨大的欺诈未遂的案件未进入统计。尽管统计结果中海上保险的欺诈案件数量很少,但这并不能归因于海上保险中被保险人的诚信程度更高。尽管对国内保险公司的调研结果显示其原因复杂而综合,但至少有两点不容忽视:一是,海上保险理赔程序中引入专业第三方公估机构的勘验和评估,以及公估机构对于保险公司委托的业务非常看重;二是海上保险更高程度的告知义务标准对于被保险人的阻吓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诚信程度较高的英国也不乏保险欺诈的案件发生。《英国保险欺诈小组终期报告》(2016年1月) 显示,保险欺诈平均每年给每个保险单持有人造成50英镑的损失,而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总共超过30亿英镑。其中,虚假陈述、未能告知相关信息和滥用合同地位都被英国保险人协会(Association of British Insurers)列为欺诈的情形。因此,以科学的法律机制来消减保险欺诈或保险标的的损失,仍是当下全球保险市场操作的执着追求。而我国海商法所规定的兜底性义务,实际发挥了安全阀的功能--违反告知义务的严重后果将起到对不够诚信的被保险人的阻吓作用。
虽然我国海商法要求被保险人承担“主动告知义务”,但对告知的范围和标准设定了限制条件。海商法第222条第2款规定,保险人在通常业务中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情形不需要告知,而根据该条第1款规定,被保险人虽然掌握该信息,但主观上不知道该信息会影响保险人是否愿意接受投保的情形也无需告知。即使被保险人对于重要情况的判断有失误而未能告知,海商法第223条仅就被保险人故意不告知重要信息的情形设定了较为严厉的后果: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不退还保险费,且不赔偿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对于非故意造成的未告知,保险人虽然有权解除合同或者要求相应增加保险费,但要免除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的损失赔偿责任,保险人要承担较重的举证责任:一是该事项属于被保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的“重要情况”;二是未告知或者错误告知的重要情况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
总之,从我国保险市场的实务操作看,我国并未出现“信息倾倒”或者“保险人滥用合同地位”的突出现象,海商法中关于告知义务的规定尚能回应实践中的争议。尽管近年来我国海上保险实务操作与英国海上保险市场有更多的相通之处,但依然存在巨大的差异。我国海商法修改所要针对的应该是立法与我国保险市场实务操作相脱节的情况。既然保险实务调研的结果显示海商法中的告知义务规定尚未对实践形成明显的制约,那么告知义务制度在当前阶段尚不需要立即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同时,英国2015年保险法中“公平陈述”是一个传统保险法的“告知义务”与合同法的“陈述”相融合的订约前信息披露机制,海商法现有的条文框架结构在借鉴该制度时具有先天的困难。但是,为避免对“主动告知”作出等同于“保险人可以坐等被保险人无限告知”的字面化曲解,我国海商法可以对被保险人“无需告知”的事项作出进一步补充:“如果被保险人已向保险人告知的信息足以令一个谨慎的保险人意识到有必要进一步询问相关情况,则保险人应该负有相应的询问义务”。
4
结语
对于最大诚信而言,英国2015年保险法堪称继1906年海上保险法之后的第二次重大立法转折,其改良了“违反诚信义务即可宣告合同无效”的单一规则模式,开启了诚信原则与告知义务等具体义务规则相结合的保险诚信制度新篇章。尽管改革后最大诚信作为指导性解释原则的法律效果有待普通法司法实践进行检验,其与我国保险法下的诚信原则在法律漏洞补充、裁判规则创造等功能方面具有基于不同法系的细微区别,而告知义务等具体义务规范也因为立法体例与实践操作的不同与我国保险立法存在较大差异,但此种“原则+规则”模式所隐含的法律思想和制度内涵却与我国保险法以及海商法呈现出趋同性。在当前保险法和海商法的诚信原则以及相关告知义务的具体规则尚未落后于海上保险实践的背景下,重构海上保险诚信制度的时机尚不够成熟。保险理论及实务界中长期以来存在的认为我国保险法或海商法中一直遵循“最大诚信原则”的理论,对我国保险法和海上保险立法中诚信义务法律内涵的解释与完善造成了困扰。保险法中的诚信的内涵及定位并不复杂,与一般商业合同法相比,其可以被解释为“高标准的诚信”。在此基础上,我国海商法可以考虑对具体告知义务的限定条件进行补充,而欺诈性索赔和迟延赔付等对我国海上保险与其他商业保险普遍适用的义务适宜在保险法中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