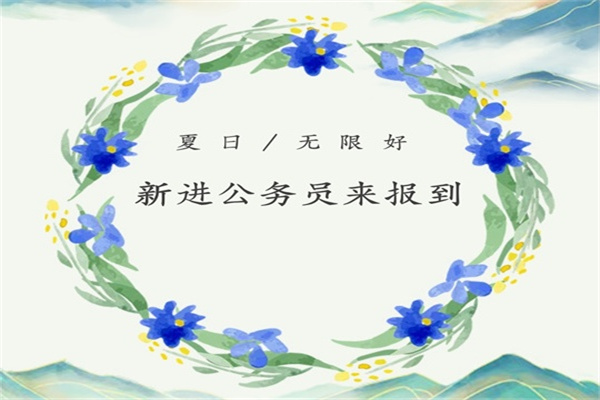民间“打会”,又名“请会”“合会”,具有筹措资金和赚取利息的双重功能,通常建立在亲情、乡情、友情等血缘、地缘关系基础上,带有互助合作性质。随着规模的扩大,有谁“得会”、获利多少,并不由“会首”掌控,使得恶性循环与不良投资行为有了乘虚而入的空间,“以会养会”“倒会”等严重后果时有发生。实践中,关于民间“打会”行为的刑法规制,司法机关往往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等问题上产生争议,以下几个问题亟须明确。
第一,亲友间的集资行为原则上不应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社会公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是认定非法集资的必要条件。通常情况下,发生在亲友间的“打会”行为由于集资对象具有特定性,人员限定于亲友圈或者单位内部人员等有限范围之内,不是“社会公众”,不符合非法集资的社会性特征。但实践中,有的“打会”行为最初是向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吸收资金,但随后吸收资金的渠道发生扩散,行为人的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开始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使得集资行为呈现社会性特征,行为性质就发生了变化,这种情形就不再属于“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而应当认定为“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
第二,“打会”人员主观“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应综合判断。一是从行为人的客观经济状况进行推断,主要包括行为人实施行为前有无足够资金以及行为后有无还款能力等因素,但因为现实中成为“会头”仅需具备“有信用、眼界宽、人缘好”等条件即可,对资金实力并无条件限制,致使这一标准对“打会”类案件适用度并不高。笔者认为,考虑到民间“打会”的特殊性,除上述因素外,更应该注重考虑行为人对于“打会”款的用途以及所选择的“打会”类别。例如,对于传统的“打会”行为,利率在一定合理范围内,“打会”款用于正常投资经营,通常不会发生“倒会”现象,就不宜认定“打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二是根据“非法占有目的”产生的时间不同,分为事前产生的非法占有、事中产生的非法占有以及事后产生的非法占有等不同情况。刑法界一般认可事前和事中主观上产生的非法占有符合主观构成要件,但由于民间“打会”这一现象的特殊性,“打会”行为刚开始因涉及的范围比较小,涉及的金额比较少,加之行为人在“打会”初期一般都比较谨慎,往往没有办法判断其是否有非法占有的故意。随着集资金额的增加,行为人对“打会”款开始表现出挥霍、任意处分等行为,事后(中)的故意更为明显。关于事后产生的非法占有故意是否符合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司法机关存在较大争议。笔者认为,应将主观故意看成一个概括发展的过程,这不仅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定罪量刑畸轻给“打会”人员造成错误的行为引导,有效规制类似违法犯罪行为。
第三,民间“打会”行为的检察应对。针对民间“打会”行为违法犯罪新动向,检察机关应当立足自身职能,充分发挥打击、保护、预防等职能作用。一方面,要提升打击民间“打会”违法犯罪活动的精准化水平,积极组织参与民间借贷领域违法犯罪专项整治活动。对于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洗钱等犯罪的,特别是一些危害范围广、社会影响大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集中力量、加大力度,依法予以打击。另一方面,在对民间“打会”行为进行刑法规制时也要有“度”,司法办案中要严格把好事实关、证据关、法律关,防止就案办案、机械办案,防止利用办案插手一般的民事经济纠纷,真正做到司法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