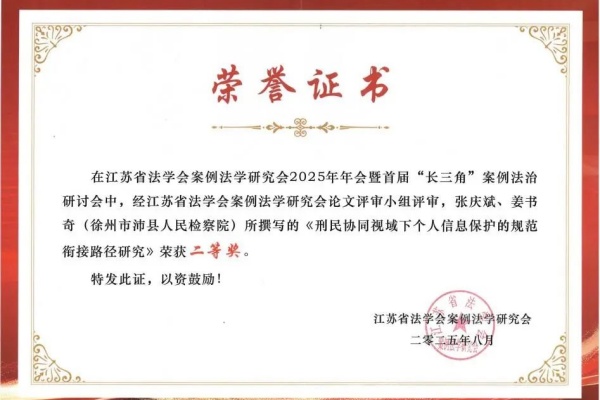近年来,为全面贯彻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逮捕程序与逮捕条件的修改,部分检察机关开始探索逮捕程序的司法化运作,逮捕的司法化程序逐渐成为司法界与理论界关注的焦点。晚近公布的“十三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围绕审查逮捕向司法审查转型,探索建立诉讼式审查机制”。针对这一审查逮捕程序的重大发展方向,笔者拟提出三个问题进行讨论,以期能进一步推动这一实践探索继续前行。
一司法化探索的宪法框架与国情
公民的人身自由权是公民权利保障体系的基石,鉴于这一定位,我国宪法历来重视逮捕程序与公民人身自由权的保障。无论是1954年宪法还是1982年宪法在宣称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后,都详尽具体地规定了逮捕程序。现行宪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我国现行的审查逮捕程序完全是按照宪法的要求构建和展开的,同时宪法将检察机关定位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地位高度司法化,与法院具有相同的宪法定位,明确要求检察权应当依法独立行使。
宪法框架是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指针,也是建立法治中国的最大国情。无论是探讨逮捕程序的司法化改革实践还是完善刑事诉讼法和执行刑事诉讼法,都应当谨守宪法框架,基于宪法规定而形成的中国司法制度,即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做法不同,在我国不是法官而是由检察官行使批捕权。检察机关的独立地位加上规范化的批捕程序,经过多年的司法实践检验证明能够落实宪法保障公民人身自由权的神圣使命,在宪法作出有权解释或者修宪之前,仍然要坚守宪法框架下持续探索逮捕程序的进一步正当化。
二何为司法化
逮捕措施的本质是对公民人身自由权的长期剥夺,是对公民重大权利的重大干预,从权利人的角度而非国家权力的角度观之,其干预效果与刑罚无异。“程序即为惩罚”,逮捕作为程序性强制措施,其本质具有剥夺公民权利的属性,唯有经过司法程序方可取得正当性。这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设专条对羁押的司法审查作出明确要求的基本道理。
我国数十年的传统观念将逮捕视为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的公权力,在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支配下,逮捕程序高度行政化,即批准逮捕的检察官主要依赖阅卷的方式单方决定是否批捕。行政化的批捕程序的弊端不仅仅是忽视人权保障,更重要的是由于缺乏兼听则明的程序,导致检察官无法全面掌握逮捕条件,进而无法保证逮捕质量,甚至可能造成错误逮捕。行政化的逮捕程序缺乏对话与沟通机制,无论是否作出逮捕决定,都易遭致当事人双方的不满,因而程序的安定性、说服力较差。
司法化的逮捕程序强调侦查机关与被追诉方双方到场,通过直接言词的方式由检察官居中听取双方意见后作出是否逮捕的决定。由于其本质是侦查阶段上的司法审查程序,在漫长的侦查过程中当出现关系到公民重大权利剥夺的事项时,嵌入特定的司法程序,体现了对公民自由权的特别关照和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
三如何司法化
在中国探索逮捕程序的司法化,既要有国际眼光又要关注中国问题,将中国国情与国际化潮流有机结合历来是有效推进制度完善的重要经验。近年来近三分之一的地方检察机关逐步探索逮捕的诉讼化、司法化的工作方式,强调同时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这些难能可贵的基层创新实践正确地诠释了刑事诉讼法2012年修改中完善逮捕制度的立法精神,值得充分肯定。当然在司法实践探索的过程中,司法实践的先行者们也出现了不少的困惑与阻力,个别检察机关的探索“昙花一现”难以长效化、持久化。顶层设计与理论指引应当进一步加强,个人认为,当前推进逮捕程序司法化运作的重点课题有以下三个方面:
1
必须破解侦查保密原则与批捕公开进行的理论难题
司法化必然要求程序公开,实务界不少人士认为这与侦查阶段的证据保密要求直接冲突。笔者并不赞同这种观点。一方面,国内对侦查保密原则的理解有待进一步澄清,即使是发端地的欧陆国家在近年来的刑事司法变迁中也在重新解释、厘定该原则的适用范围,最佳例证为2012年欧盟通过的被追诉人信息知悉权指令中已经明确要求欧盟成员国在决定羁押时应当事先告知辩方所有的侦查证据与材料。另一方面,审查批准逮捕程序本身不是侦查程序,而是侦查阶段上的司法审查程序,在审查批捕的过程中应当奉行司法权内在的机理,而非遵守侦查程序的相关原则。
2
逮捕程序的司法化运作应当正确定位司法过程中的控辩审三方关系
对于检察官,应当通过司法改革进一步赋权其基于直接言词原则的司法过程直接作出决定的职权,同时还应强化其以司法方式处理案件的相应技能,比如居中主持、控制听审节奏、明确争议焦点等方面,长期行政化模式运作的检察机关在这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对于作为控方的侦查机关,应当根据法律与司法解释的要求,承担举证责任、提供更多信息并积极参加司法化决定过程;对于辩方而言,需要进一步研究值班律师或法律援助制度的强化和被告人本人需要在场的各类情形。
3
逮捕程序的司法化探索需要顶层设计与基层首创紧密结合
伴随着目前实践探索的逐步深入,顶层设计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中央有关决策机关应当适时出台相关规范性、指引性文件,一方面,要为这一探索提供配套支撑,重点关注逮捕工作的考评指标体系、国家赔偿制度的完善。另一方面,结合目前正在进行的检察权运行机制改革,在批捕检察官及办案组织问题上做好优化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