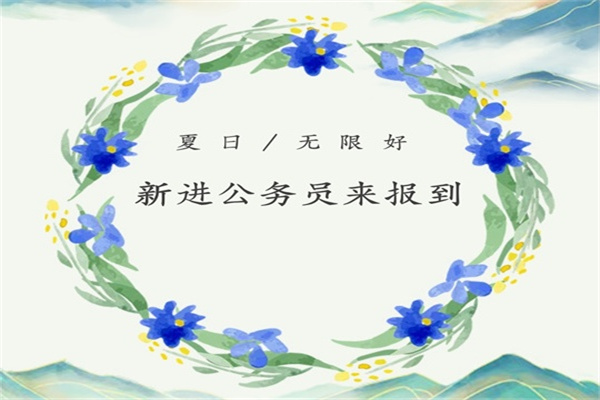编者按:
为丰富我国检察学和少年司法理论体系,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检察制度,中国检察学研究会未成年人检察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构建中国特色未成年人检察制度体系研讨会于2016年10月17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未成年人检察面临的挑战”“未成年人检察的组织体系建设”“未成年人检察职能整合”“中国特色未成年人法律体系及少年司法保护体系建设”以及“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1
关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面临的挑战
经过30年的发展,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以下简称“未检工作”)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形成“捕、诉、监、防”一体化格局,成为检察机关不可或缺的重要业务之一。但也应当看到,未检工作还处于发展阶段,从法律体系到组织机构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北京市检察院副检察长苗生明表示,制约未成年人检察科学发展、统筹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正逐步显现:第一,在最高检统筹下,捕、诉、监、防等方面涉未刑事办案职能已实现统一,但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执行检察、民事行政检察等还分散于各个部门,碎片化问题依然存在;第二,绝大多数检察院的未成年人案件量较小,难以形成规模,但把大学生犯罪、所有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均纳入未成年人检察领域,又背离未检工作的宗旨;第三,未检部门人员编制有限,但职能却呈现多元化,造成多样化的专业性需求与过少的人员组织支撑不相协调。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院长姚建龙教授认为,未检工作还有许多根本性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第一,未检的外部成长环境仍然非常艰难,以成人法为框架的法律体系无法给予未检制度良好支撑;第二,未检的职能定位不明,从最初的起诉单一制,到捕诉双职能,乃至如今的五项职能,名称始终处在变动之中;第三,未检的理论体系很不成熟,理论明显滞后于实践发展,难以及时回应实践诉求。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校长林维教授通过对实证数据的定量分析,认为未检工作正面临比较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是未检队伍的扩张,另一方面却是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数量的减少,两者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要求未检必须在受案范围或工作职责等方面作出调整,以应对未成年人犯罪态势及刑事政策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宋英辉教授认为,建立健全独立未检业务类别是未检工作的立身之本,如果按照成年人案件的管理模式去管理未成年人案件,未检的独立业务类别将很难实现;如果未成年人案件的评价指标与成年人案件相同,未检的独立业务类别也很难获得足够支撑。北京市检察院未成年人案件检察部主任岳慧青认为,我国未成年人检察的法律体系还很不牢固,缺少专门的少年刑事法、儿童福利法,少年法院等专门机构建设仍在艰难探索中,配套的少年警务和社会支持体系很不完善,学术界也没有将少年司法纳入主流研究领域。
2
关于未成年人检察的组织体系建设
当前,在最高检的大力推动下,全国性的未成年人检察组织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北京市检察院在本轮司法改革中全部保留三级未检机构,并将未成年人案件检察处更名为未成年人案件检察部,为未检工作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史卫忠表示,全国省级检察院已经建立或者编办已经批准的正式未检机构达到20个,根据最新统计,在2016年年底之前,绝大多数省份都可以成立独立的未检机构。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院长卞建林教授认为,未成年人检察实践要有专业机构,北京市检察机关在司法改革的浪潮中保住未检机构和队伍,并迎来蓬勃发展,为全国检察机关做出了表率。宋英辉认为,办理未成年人案件,要同政府部门对接、同群团组织对接、同专业社会机构对接,必须由专门机构来承担,在司法改革扁平化管理的背景下,强调未检机构的独立性,是尊重司法规律的要求。苗生明提出了创设少年检察院的构想,国外很多地方主要是设立少年法院,但在中国的司法制度中,检察机关承担批捕、起诉、监督等职责,事实上检察院在未成年人检察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少年法院、少年检察院共同设立,才能形成自成体系、互相对应的机构。建立少年检察院有利于未检职能集中整合、未检案件集中管辖、未检人员集中管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敏远认为,未成年人保护机构的设置要成体系,若不成体系,只考虑某一环节、某一方面,效果会比较有限。上海市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处长吴燕认为,对于未成年人案件数量比较少的地区,集中管辖模式是确保未检机构独立性的次优选项,建立少年检察院对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也极具诱惑力,但集中管辖会造成检察机关在协调非本行政区划内公安机关的未成年人工作时难度较大,无法保证效果,也难以调动非本行政区划内的各方资源开展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应当重视这些问题的解决。岳慧青认为,只有建立少年检察院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案件量、评价标准、考核等一系列问题,而对于地广人稀、案件量极少的地区,可以探索少年法院派出法庭、少年检察院派驻检察室等方式。
3
关于未成年人检察的职能整合
全面保护、综合保护是未成年人检察的发展方向。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龙翼飞教授认为,我国的法律制度已进入人类法治文明的第三个阶段,即回应型法律阶段,应当回应未成年人在我国社会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法律保护遇到的障碍,以及如何运用检察机关特有的职能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相应的法律支持。吴燕认为,当前调整未检职能范围的基本思路是将检察机关涉及未成年人的业务全部划归未检部门,这也符合未检专业化的发展方向,但将已满18周岁的大学生犯罪纳入未检部门受案范围,难以体现特殊司法保护,可能弱化未检职能;对于未检部门办理的未成年人案件,当事人向本院提出申诉的,若未检部门继续承办申诉业务,则有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之嫌;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一般预防也要注意适度参与,不能喧宾夺主。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林艳琴认为,国际公约及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为民事检察制度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实施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但民事检察权的行使应当以社会自治和公民自治优先为总体理念,有效平衡国家干预与意思自治、公益维护与私权保护之间的关系,避免公权力对社会民事活动的不当干预,防止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对私人合法权益的不当侵蚀。暨南大学教授张鸿巍从中美少年司法比较的角度切入,认为未成年人遭受虐待、遗弃的案件,与家庭暴力有较大关联度,直接涉及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内容,可以积极探索延伸检察职能,拓宽检察院的受案范围,因此,家事检察大有可为。姚建龙提出应赋予检察机关先议权,将虞犯少年案件、违警案件、触法案件、犯罪案件均纳入检察机关受案范围,建立社会处分、保护处分、刑罚处分为一体的三级处分体系,并主张未来应以法律监督权为中心,建立未成年人保护的监察体系。
4
关于未成年人法律体系与司法保护体系建设
健全的未成年人法律体系,是衡量一个国家未成年人保护水平的重要指标。目前,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难以紧跟时代步伐,某些重点领域、薄弱环节问题还较为突出,如儿童福利基础性立法缺失等。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高维俭认为,未成年人立法应当包括少年福利法、少年保护法、少年案件处理法三个方面,少年福利法是未雨绸缪之策,却面临结构性缺失;少年保护法则存在机制性缺憾,犹如“九龙治水”,很多部门都可以管,但很多部门都没有管到位;少年案件处理法是亡羊补牢之策,尚有待于系统、科学的提升。岳慧青认为,应当抓住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修改及民法典编撰的契机,明确少年检察、少年审判的组织法地位,并将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内容纳入进去,同时,考虑增设法律条文,将轻微违法犯罪、不满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通过检察环节的暂缓起诉,采取强制工读、强制收容、禁止令等多种方式进行教育矫治,以便为中国特色未成年人检察制度的构建提供良好的法律基础。吴燕认为,刑事诉讼法已经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但是关于帮教矫治、保护处分、亲职教育、犯罪预防等方面的实践做法亟待法治化,且未检制度的构建不能仅仅局限于刑事诉讼立法,还应将视野扩展至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其他领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顺安建议加快少年立法进程,科学立法,同时主张建立统一的保障少年法实施的行政执法部门。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党组书记操学诚认为,构建中国特色未成年人检察制度要与十八大以来构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与司法体制改革,特别是司法制度建设有机结合,把未成年人检察和未成年人法院、警务有机结合,形成一个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体系和司法保护体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任士英建议加强少年警务建设,认为少年警务应当体现出侦查权的强力特点,将帮教前移到侦查阶段,通过参与社会调查、审前羁押、训诫等一系列活动,用侦查权的实施达到教育、挽救的功能,从而使涉罪未成年人在侦查环节得到教育挽救。同时,要评价未成年人案件的特殊程序、教育矫治、帮扶情况,推动少年警务的健康发展。北京市高级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庭长赵德云指出,目前全国高级法院仅有4个成立了独立建制的少年审判庭,发展比较缓慢,而少年家事审判改革是需要顶层设计的问题,所谓唇齿相依,检察机构的发展也受少年家事审判改革的影响。
5
关于未成年人检察的社会支持体系建设
未成年人检察是一项系统性工作,有赖于社会各界通力协作,检察机关不能单打独斗,必须吸纳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共同参与防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卞建林认为,未成年人检察不能管得太宽、太严,还是应该属于家长的问题归家长、属于学校的问题归学校、属于社会的问题归社会、属于国家的问题归国家。姚建龙通过对未检发展历史的分析表示,未来应当通过转介机制来连接少年司法体系和少年司法的支持体系。操学诚认为,可以发挥检察机关专业化的影响力,将检察职能与社会司法保护和社会预防相结合,并向前延伸,成为社会专业队伍的孵化器和平台。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倪春霞提到民政部门正在大力推动三社联动,即社会组织、社工、社区“三位一体”保护未成年人,下一步还要借助慈善法出台和中央关于有序推动社会组织发展的机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为司法机关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提供良好的社会支持服务体系。王敏远认为,未检工作需要专业的知识体系,除了法律方面的知识,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也要运用到未检工作中来,各方面人士的参与很有必要。赵德云指出,北京市检法两机关联手,依托首都综治平台,联合公安、司法行政、民政、教育、人力社保及社工组织等,构建了1+6+3的配套体系,包括社会调查、合适成年人参与、犯罪记录封存、心理疏导救助等,提升了整体的未成年人保护水平。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从法律援助的视角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支持体系建设,一方面法律援助的范围要扩大,另一方面法律援助人员的职业化、专业化方面需要发展,因为律师自身如果不专业,就难以保障未成年人的权利。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理事长宗春山结合脑科学研究成果指出,青少年犯罪行为,跟大脑内部分泌的多巴胺有重要关联,多巴胺水平的提高,驱使青少年对高刺激、强烈的东西产生兴趣,社会力量应当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方面提供专业的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