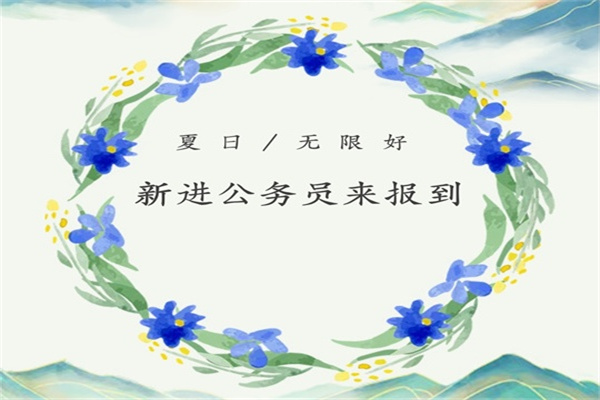实践中,重大事故特别是涉及危化品的事故不仅会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并且将对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以及人居环境造成持续的、不可逆的危害。但是,现行立法关于重大事故的刑事责任追究中,较少提及环境责任的承担。笔者拟从刑事责任层面对重大事故环境责任承担进行分析,为环境保护刑事立法的推进提出意见和建议。一、污染环境罪的立法缺陷
我国污染环境犯罪相关规定在面对重大事故引发的严重环境问题时存在疏漏之处,难以适应当前环境保护的实际需求。随着近年来环境保护需求的不断加强,对污染环境犯罪的惩处力度需要相应加大,应积极推进环境违法行为量化标准制定,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定性定量分析,为入罪确定合理标准。
(一)对污染环境罪的刑事规制体系不够严密
刑法修正案(八)通过修改犯罪客观要件,降低了污染环境罪的入罪门槛,扩大了刑事责任追究范围,有助于更有效地惩治污染环境犯罪。但是针对污染环境犯罪刑事规制的立法体系仍存在体系粗疏、留白过多、缺乏兜底性规定等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污染环境罪入罪标准过于模糊、失之于宽。从重大事故的环境责任追究可行性角度来看,基于我国污染环境犯罪仅规定了故意倾倒污染物造成环境损害的情况,无法认定涉案企业及责任人故意违规存储危化品、污染物致使造成突发性严重环境污染事件的刑事责任。若以举重以明轻的刑法原则进行认定又容易陷入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尴尬境地。导致发生该类事故后难以选择合适的条款对重大事故责任人追究相关环境污染刑事责任,进而造成对重大事故环境责任追究“选择性忽略”的情况发生。
(二)污染环境罪构成要件存在疏漏
囿于现行刑法立法的不足,即使能够明确认定重大事故中环境污染确系责任人故意为之,也很难对行为人进行相应的处罚。为此,笔者认为,根据当前立法的实际情况以及污染环境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可以采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作为兜底条款,对重大事故中主观恶意明显、犯罪手段恶劣、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行为人(自然人)以该罪论处,彰显刑法打击犯罪的功效。
与此同时,我国现行污染环境罪大多属于结果犯,而立法上缺乏对污染环境危险犯的规定。以教训十分深刻的天津港爆炸事故为例,天津港爆炸发生前,涉案公司在数年的时间里不断违规扩大危化品的堆放区域,不经合法审批,擅自违规经营,危化品一旦发生事故势必对环境造成严重危害,而对于这种情况依据现行刑法无法进行规制。污染环境罪主要以过失犯罪为主,污染行为入罪门槛上相较故意犯罪而言更为严苛,即行为人需要造成严重的环境危害方被纳入刑法规制范围之内,导致刑法对环境污染行为的过度宽容,与刑法目的严重背离。
二、完善污染环境罪的刑法规制
对于污染环境罪立法的完善,首先应当着力推进污染环境罪罪名的完善,设置与过失犯罪相对应的故意犯罪罪名,同时研究设立单位犯罪,将其纳入到立法规划之中,进一步完善刑罚体系。
(一)调整具体罪名设置
基于环境污染治理的严峻形势及当前我国对污染环境罪采取的惩处模式。笔者认为,可以将污染环境罪改为“过失污染环境罪”,并设置相对应的故意犯罪,罪名可直接称之为“故意污染环境罪”。通过明确污染环境犯罪的故意形态与过失形态,设置不同的犯罪表现形式以及量刑区间,拉开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的量刑尺度,区分对不同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完善污染环境犯罪刑法规制体系。
(二)以危险犯作为污染环境罪的犯罪形态
传统理论认为,污染环境行为只有产生了环境污染的危害后果,才能对其进行定罪处罚。然而,当前环境污染不断威胁人类的生存环境,加大环境保护力度迫在眉睫,对污染环境行为的事前规制殊为必要。对污染环境罪行为与结果间的因果关系可引入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加以认定,但在其适用过程中应受到限制。从应然角度分析,应将污染环境罪构成要件的认定由结果犯改为危险犯,污染环境罪事实上是一种危险状态,刑法应对该种危险状态持负面态度。从实然角度分析,将污染环境罪确立为危险犯能够更好地适应事前惩戒机制的确立,更符合实质正义的实现。
笔者认为,针对污染环境罪应秉持“预防为主”的基本原则。应对将环境置于污染危险境地的行为认定为犯罪构成的基本形态,将发生危害后果、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作为法定刑升格要件。实现事前预防与事后惩处的有机结合。
此外,现有污染环境犯罪普遍以长时间、积累性的污染行为作为规制对象。从立法体系完善的角度考虑,对重大突发的环境事故可以增设重大环境事故罪,该罪可以将一般主体因主观故意或者造成重大事故引起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等情况纳入到其规制范围内,且保持与重大责任事故罪相同幅度的量刑。一方面能够确保重大环境事故能够纳入到刑法规制范围内,另一方面可以扩大污染环境的刑法规制范围和处罚力度。
三、完善污染环境罪的处罚体系
首先,统一污染环境罪的法定刑标准。犯罪惩处的法定刑标准不一,容易出现“同案不同罚”的现象,进而滋生权力寻租空间以及出现“法律洼地”现象,对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环境保护产生负面影响。
其次,污染环境罪法定刑幅度偏低。根据刑法罪责相适应以及罪刑法定原则,在不突破现有法定刑上限的情况下,应将量刑基准确定为中间刑期以上并慎重适用缓刑。即便需要适用缓刑的,亦可搭配禁止令共同使用,以降低乃至杜绝犯罪分子再犯的可能性。
再次,应加大财产刑在污染环境犯罪中的适用比例和适用金额。应当看到,一方面,环境犯罪产生的直接后果是造成环境污染。另一方面,行为人意图通过污染环境的破坏行为获取不正当利益。多数污染环境罪的犯罪动机是出于追究高额的经济利益,对此可以通过高额的罚金促使行为人打消犯罪的念头。具体而言,一是进一步明确罚金的具体计算公式,建议可以参照逃税行为的惩处模式,以行为人获利或造成损害的数额为基准,施以二至五倍的罚款。二是对于故意实施污染环境犯罪行为的,可以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或部分财产,增加对行为人的威慑力,起到有效惩治和预防犯罪的功效。
最后,对污染环境罪应当结合现有刑罚体系,采用多元化的处罚机制,最终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具体可以采取罚金刑、自由刑、社区矫正相结合的刑罚模式,对于重大责任事故环境责任承担中的主要责任人员采取罚金刑加自由刑的刑罚模式,对于其他责任人员采取罚金刑加社区矫正的刑罚模式,在社区矫正的过程中要求被矫正人员学习环保知识、参与环保工作、进行环保宣传,使其充分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从而实现刑法的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相结合的目的。